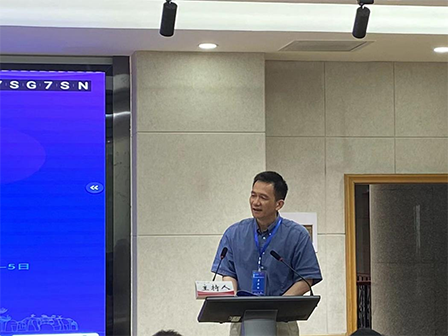作为博弈规则的法律--写在前边
书刊 · 2004-07-19 00:00
返回法律出版社的高山君,要我为《法律的博弈分析》第二版的发行写一个东西。恭敬不如从命,况且也是我最喜欢的领域,假装推辞一下也就欣然接受了。但漫无边际写来,还请旭阳兄和读者诸君指正。 我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强调博弈论在法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
法律出版社的高山君,要我为《法律的博弈分析》第二版的发行写一个东西。恭敬不如从命,况且也是我最喜欢的领域,假装推辞一下也就欣然接受了。但漫无边际写来,还请旭阳兄和读者诸君指正。
我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强调博弈论在法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与此有关的是,博弈论的方法工具在什么意义上是对人类行为的合理描述?这本《法律的博弈分析》有什么特色?
统一的社会科学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成果之一,博弈论(game theory)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人类社会运行模式和制度建构的思考。由于博弈论的抽象性、统一性和普适性,它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物理学”。随着其理论体系的牢固建立和成果的不断涌现,它在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学科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并且借法律经济学的兴起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进入法学领域。所以说到法律与博弈论的关系,就不能不涉及到法律经济学,也就必然涉及到法学和经济学这两个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之间的关系。
原则上,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所谓的法、道德、经济、政治等概念是我们用以描述世界的符号,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划分只不过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或者归咎于我们对整体的无知而不得已的选择(盲人摸象的故事说明了这点)。所以,我们能看到,现代社会科学表现出两个看似冲突实则协调的发展趋势,一是研究主题的不断分化加细,二是研究方法的综合交融。前者是学术分工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非如此不能有学术的进步和繁荣;后者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反映,理论工具的一般性体现了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结构模式上的深刻联系,也是科学理论简洁、精致的审美观的要求。
法律作为人类社会自组织的一种制度方式,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架构,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几乎各个角落。但是,作为问题导向的学科,法学自己本身几乎没有特殊的研究方法,它的大部分工具都是从其它学科借鉴来的(虽然这丝毫无损于其论题的头等重要)。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法学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吸收借鉴了大量研究方法和观察世界的视角,并以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反哺于其它学科。翻开一部法学思想史,理论大家少有法学院系科班出身者。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许多法学家在哲学、经济学甚至数学领域造诣颇深。英国有一段时间还真出现过不少数学家都在读法律学位的情况,因为搞法律比起数学来钱要容易挣得多。
那么,什么力量使得下述情况出现呢?在当年亚里士多德那儿只被叫做“家政学”,从亚当•斯密算起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经济学,后来居上地成了“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甚至暴露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倾向而到处摧营拔寨、攻城掠地,以至于使其在法学界的最大“俘虏”——波斯纳大法官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法学家,而他当年的助手,曾任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现为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的理查德•莱西格竟然说(见苏力“《波斯纳文丛》总译序”):“如今,我们全都是法律经济学家了!”
原因在于,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已经脱胎换骨。萨缪尔森在其经典教科书中曾谈到,经济学是关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学科。这个说法,在当时可能是恰当的,现在却显而易见是不全面的。今天我们似乎有理由说,经博弈论改造过的实证微观经济学,业已发展成为一个超出经济分析领域的框架,成为关于人类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式的一般性理论。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就在于它根据资源稀缺和理性人等基本观念,最早尝试并部分实现了前述社会科学的统一性,而其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博弈论和个体理性决策(individual rational decision)。
容我说句可能很多经济学家也未必接受的话,与法学一样,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制度。因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无外乎描述社会如何存在运行的实证理论和应该如何的规范理论,二者的结合则有种种所谓“改造世界”的政策主张和制度建构。在微观经济学里,也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机制设计文献里的Mount-Reiter三角),即个体理性决策与博弈论、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和机制设计(mechanism design)理论。我可以举两本现在欧美最流行的教科书为例,表明并非是节外生枝或故弄玄虚。其一是哈佛大学的马斯-科莱尔、温斯顿和格林的《微观经济学》,其二是扎西尔和雷内的《高级微观经济学》。
把这些工具和方法应用于法学,我们就看到,博弈论为法学提供了一个实证理论基础,它描述人们在一个制度环境(博弈规则)下是如何做出行动决策的,这些行动导致了什么结果;社会选择理论则集中于分析社会如何逻辑一致地从个体偏好中得到合理的社会目标,这个过程中应该体现哪些价值标准以及如何解决不同价值准则之间的折中——法学中的话题叫社会公平或正义;而机制设计理论探寻的则是,一旦我们确定了社会目标,那么可以设计合理的制度(法律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使得在这个制度下人们博弈的结果尽量处于或接近社会目标集合。
读者诸君自然明白,这是个具有普遍性的统一框架。这种分析问题的框架,不是说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要想逻辑一贯地解决问题,我们就只有这样去考虑问题。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不是教你不胡说,而是教你一种精致的胡说”。
法律作为一种分散决策机制
至少在规范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法律看作一种机制设计。而作为社会选择和博弈论的自然结合,机制设计理论面对的是一个分散决策(decentralized decision) 问题。
从社会选择理论我们知道,如果存在一个社会选择函数(或对应),那么,在任何一种情形(自然状态)下,针对个人偏好组合,我们都有一个或几个社会方案是我们认为合理的。但这是从一个客观观察者或研究者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如果社会的设计者(designer)或计划者(planner)、执行者(implementor)、仲裁者(arbitrator),象客观观察者一样,具备对社会的足够知识和信息,那么一个简单的集中的强制性机制(只要是技术上可行的)就会实施任何所谓合理的社会目标。但是,真正有意义的是,设计者或执行者不可能具备这么完全的知识和信息,或者有些信息是他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使用的,或者信息是可观察的(observable)但不是可核实的(verifiable)。这时需要探讨的是,如何使得通过社会选择函数表现的社会目标能够实现。机制设计理论把这个问题转化为,假设设计者知道社会选择函数而非特定自然状态本身是合理的社会目标,知道社会中的行为模式,即每个人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以及任何行为组合会导致的结果,那么,我们只需要设计一个制度框架,譬如财产权利、契约法律、投票法律和投票规则甚至宪法等诸如此类,使其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从而间接实现社会目标。
作为一种典型的通过分散决策以实现社会最优的间接控制模式,法律背后的思维至少应该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三位一体框架。如果我们不想仅仅成为一个对现行法律的注释者,还要尽量推动它们的改善和进化,那么我们就“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们不仅要知道已经被设计出的制度是怎么样的,我们还要知道它是如何被设计出的,它应该被如何设计。除了博弈论观念通常蕴涵的可行性、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原则以外,这里我们再罗列几个重要的机制设计观念:信息与知识复杂性约束;稳健性;策略性模糊。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何谓合理社会选择函数以及它所确定的社会目标?博弈论在何种意义上是对人类行为的恰当描述?前者不在此处多说了,我们请大家参考黄有光的《福利经济学》和缪勒的《公共选择》,正如机制设计方面的成果参见考尔肯的《经济学中的社会最优决策的执行理论》,后者则要浪费一下读者的眼球了。
作为社会物理学的博弈论
一位物理学家魏扎克说过这样的话:“自然比人类更早,而人类比自然科学更早”。没有博弈论的时候,人们已经在进行着博弈了;但有了博弈论,未必人们就一定赢得更多。我们说博弈论是社会物理学,是因为我们认为博弈论反映了一种直觉上合理的观察、描述和解释社会的途径。
首先要说明的是,博弈论建立在个体理性决策(所谓一人博弈)理论的基础上。一般地,我们说一个人理性地选择其最优行动,只要按照他的信念这个行动最大化其预期效用函数(Kreps,1987)。作为研究“理性人的互动行为”的学科,博弈论至少有四个基本特征(我抄一下讲义):
群体性(group),我们生活在二人以上的世界里,只要我们不是鲁滨逊;
互动性(interaction),事情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所有人的行动;
策略性(strategic),每个人都认识到并考虑到这种相互依赖性;
理性(rationality),所以每个人选择行动的时候要针对对手的可能行动(所谓关于对手的信念信念)而选择一个最优对策。
只要我们关心的问题场景满足这几个特征,那么博弈论就能派上用场。决定每个人如何行动,或者说博弈如何玩法的,就是解概念。它们本质上依赖于博弈的物理结构(包括博弈者集合、每个博弈者的行动集合、支付函数、谁在什么时候行动以及此时他知道什么)和知识系统(博弈者关于博弈结构和其他人的理性程度的知识以及关于这些知识的知识,等等)。最重要的解概念——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意味着这样一个行动组合(严格来说是策略组合):在其他人不改变行动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没有动力选择其它行动。在行为方案与信念系统的相互支持下,这个均衡就是一个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的行动方案,或者说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一个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预见。所以,均衡是个“进去就出不来”的定态。你可以想象我们是武侠小说里的两大高手,最后一切招数都不管用了,只好以比试内力一决雌雄。这时即便你想撒手不干也欲罢不能,因为我的内力正源源不断向你攻来,你一撤内力则非死即伤;我呢,处境一点儿不必你强。我们两个这样僵持的局面就是一个纳什均衡。
这里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囚徒困境的改写版来说明一下。假设你和我在一个法治不是特别健全的社会里打一场官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以一定金额(你还可以考虑贿赂金额可能不同的稍微复杂的情形)贿赂法官或不贿赂。如果我们都不贿赂,那么他会给出一个基本公正的裁定;但如果有一个人贿赂而对方没有,自然是没有贿赂的倒了大霉;当然如果我们都贿赂了法官,那么两下里扯平,只不过钱就白花了。所以,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也是占优策略均衡)就是,我们两个都会理性地选择贿赂法官,然后出现“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结果。
纳什均衡等解概念(请参考那些博弈论教科书和百科全书式的《博弈论手册》)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博弈将如何进行的合理描述?这是博弈论解概念的基础问题,至少有两方面特别重要的回答。其一是我们刚才已经涉及的演绎的或知识论的解释,也就是所谓经典博弈论的解释,关于“普遍知识”(common knowledge)的文献大多集中于此;其二是进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的解释,我们把解概念看作是不那么理性、不那么聪明的博弈者(譬如动物或植物)在长期试错、学习、调整和适应过程中的“极限结果”或“平均分布”,即达尔文所谓的“适者生存”。
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两个互补的观念。公孔雀总是张开又长又漂亮的尾巴在母孔雀身边炫耀。进化生物学家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示意(signaling)机制,公孔雀好像在说:“森林里树枝那么茂密,天敌又那么多,而我拖着比别人又长又大的尾巴还活得好好的,说明我比别人都更聪明而强壮。嫁给我,你的基因就会更有可能得到传播,因为我们的后代会同时继承我的基因而更容易生存。”哈耶克曾言,“理性是我们进化的产物,而不是相反”。我们一般说那些在进化中生存且稳定下来的行为就“好像是” (as if) 具有很好的理性和知识一样的行为,那些事后来看被有效实施的制度(譬如习俗、惯例)就好像是事前被精心设计出来的,这也就为研究者采取这样一种描述或解释世界的方式提供了合理性辩护。
正如有人批评理性预期学派,运用大量数学和信号处理工具来描述行为者是如何做出理性预期的,而现实里的人未必会懂得那么多的数学去做类似的计算。我们有必要知道其创始人之一穆斯的回答:鸟不懂空气动力学,但它依然飞得很好。要研究鸟的飞行,却不得不借助于空气动力学,我们只得假设鸟是像懂空气动力学一样飞行的。我们研究人类行为时,一定程度上采用严格的形式化语言建立博弈模型,是因为我们往往可以假设人们“好像是”与模型所说的一样行动,当然这要看我们怎么构建模型以及我们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由于机制设计主要是从长期和统计意义上考虑问题,我们可以认为纳什均衡及其精炼是比较能被接受的解概念。
什么是合宜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多大程度上有用?我们先听听一个博弈论的领军人物鲁宾斯坦的看法:“一个模型是我们关于现实的观念的近似,而不是现实的客观描述的近似”。这可能会招致主张社会科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人物的批评。我想,通过适当的分析处理,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冲突是似是而非的。这并不是说现实世界不重要。正因为现实世界重要,我们才关心我们是如何理解现实世界的。本质上我们所有理论都是通过构建模型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只要我们按照某种标准较好地刻画我们关于现实的观念(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我们就会收获到作为副产品的“对现实的客观描述的近似”。
博弈论本身是一个数学分支,有不少人对社会科学的数理倾向以及背后的理性人观念表示怀疑甚至鄙夷。误解之一是:数学意味着定量描述。实际上大部分数理经济学是用数学方法作定性的研究,而量化处理的任务往往由计量经济学来做。在很多情况下,定量描述是不必要的,我们只关心那些结构性的关系即可。损害赔偿中赔偿多少最终必须拿出定量方案,而谁承担举证责任和赔偿责任则是定性的问题。
误解之二是:数学能完备地解决问题吗?实际上数学里就有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形式化不能穷尽数学,并且哥德尔之后数学家照样用形式化方法研究数学。既然我们命中注定得不到终极完备的理论,那么关键就在于做了,要不我们为什么经常听到老师教导我们“你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
所以,在有人嘲讽“数学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反问一句“不用数学又能做什么”的。数学对社会科学仅仅是一种工具(奥斯本和鲁宾斯坦在他们的“前言”里面就指出,不用数学也能写出一本关于博弈论的书来),在运用这种工具解释社会的过程中,其脆弱性正如罗素对数理逻辑的自我嘲讽:满篇的数学符号只是吓唬外行粗鲁涉足、贸然发言的防御工事,真正的核心再简单不过,简单得我们甚至能在直觉上判断它(它的力量在于它严谨的逻辑,而它的阿喀硫斯之踵在于,如何选择可信的公理化预设)。我们也见过太多矫揉造作的数学模型,其实际价值一点儿不比文字描述所构建的“模型”更实用。但博弈论这种数学形式的社会物理学(在我看来)是如此美妙和有力,轻言放弃未免武断。因为你不去发展它就永远看不出它多大程度上有用,并且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假设我们不涉及一个自我相关问题,即我们不考虑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博弈论研究,而仅考虑作为解释世界的工具的博弈论。毫无疑问,从影响现实世界的角度,可能用文字表达的法学和经济学比用博弈论的数学语言表达的更有力。我不认为运用数学是我们唯一可能或应该的生活方式。如果强求这样,我们可能就为了某种不必要的严格性而失去了生活的多样性,这可能本身就不是一种理性或明智的生活态度,我们有变成森所谓的“理性的傻子(rational fool)”的危险。但我认为这最终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很强的理由劝说别人如何生活。
从这本书中能学到什么?
一般人都爱说“放在最后的未必是最不重要的”。该轮到为这本《法律的博弈分析》说几句好话了。
一项法律会引申出一套博弈规则,签订一个契约也就进入一个博弈。在很多早期的法律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往往看不出对相应的博弈的准确表述。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对地地道道的法律问题的原汁原味的博弈论分析。我有两点个人的心得。一是,我曾仔细推敲过最后一章“讨价还价与信息”中的模型,写得真是丝丝入扣、细致入微。二是,第六章“集体行动、嵌入博弈与简单模型的局限”特别强调了,要慎重选取一个合宜的模型来描述或解释一种特定现象。这是一些博弈论教科书也容易忽略的地方,反映出作者们对博弈论理解的精深。岳飞这样谈到兵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逻辑上讲对任何现象几乎都有无穷多可选择的模型,但到底采用哪个可就是区分高手和庸才的地方了。
本书1992年英文版的问世应该是法学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甚至还进入一位经济学家沃尔克(Paul Walker)编的博弈论历史。套用马克思的话,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律经济学只有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的时候,才是真正达到成熟和完善的地步。
附:几本相关参考书和教材: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Robert Aumann & Sergiu Hart(ed.) (1992, 1994, 2003): Handbook of game theory with economic applications, vol. I, II, III, Elsevier Science B. V.
Ken Binmore (1994): Playing fair: Game theory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volume I), MIT.中译本: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一卷):公平博弈,王小卫、钱勇译,韦森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
Luis C. Corchon: The theory of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ly optimal decision in economics.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Drew Fudenberg & Jean Tirole (1991): Game Theory. MIT Press.中译本:弗登博格、梯若尔:博弈论,黄涛等译,姚洋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Robert Gibbons (1992): A primer in game theory, New York : Harvester Wheatsheaf.中译本:吉本斯:博弈论基础,高峰译,魏玉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黄有光:福利经济学,周建明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
David Kreps (1987): Notes on the theory of choice, Boulder & London: Westview Press.
Dennis C. Mueller (2003): Public choice 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第二版中译本:缪勒:公共选择,杨春学、李绍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Roger B. Myerson (1991):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中译本: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于寅、费剑平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
Martin J. Osborne & Ariel Rubinstein (1994): A course in game theory, MIT.中译本:奥斯本、鲁宾斯坦(2000):博弈论教程,魏玉根译,高峰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ric Rasmusen (1994): Games and inform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second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中译本:拉斯缪森:博弈与信息,王晖等译,姚洋校,北京大学出版社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