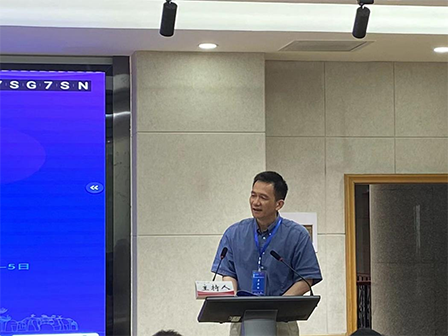萧条经济学
书刊 · 2009-03-10 00:00
返回但凡思考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那是一场无妄之灾,而不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他们认为,假如当年赫伯特?胡佛没有在经济萧条迫在眉睫时还试图保持预算平衡,假如当年美联储没有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来维护金本位,...
 但凡思考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那是一场无妄之灾,而不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他们认为,假如当年赫伯特?胡佛没有在经济萧条迫在眉睫时还试图保持预算平衡,假如当年美联储没有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来维护金本位,假如当年政府官员迅速向境况不妙的银行注资,以平复1930~1931年间蔓延开来的银行恐慌,那么1929年的股市崩溃将只会引发一场普普通通的、很快被人遗忘的经济衰退。他们还认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已经汲取了教训。如今的财政部长再也不会重提安德鲁?梅隆当年的著名建议:“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民、清算房地产……将腐坏因素从经济体中涤荡出去。”所以,像“大萧条”那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但凡思考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那是一场无妄之灾,而不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他们认为,假如当年赫伯特?胡佛没有在经济萧条迫在眉睫时还试图保持预算平衡,假如当年美联储没有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来维护金本位,假如当年政府官员迅速向境况不妙的银行注资,以平复1930~1931年间蔓延开来的银行恐慌,那么1929年的股市崩溃将只会引发一场普普通通的、很快被人遗忘的经济衰退。他们还认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已经汲取了教训。如今的财政部长再也不会重提安德鲁?梅隆当年的著名建议:“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民、清算房地产……将腐坏因素从经济体中涤荡出去。”所以,像“大萧条”那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真的是这样吗?20世纪90年代晚期,一些亚洲经济体遭遇了一场经济萧条,这些经济体的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其总人口约为6.67亿。诡异的是,这场萧条与“大萧条”颇为相似。像“大萧条”一样,这场经济危机的爆发犹如万里晴空一声霹雳,甚至在萧条已初现端倪之时,大多数专家学者还在预言这些国家的经济会持续繁荣;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为了应对危机,人们使用了传统的经济药方,但发现于事无补,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在现代世界里发生,这理应让所有有历史感的人不寒而栗。
我当然也不例外。本书的初版就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而写的。虽然有些人将亚洲危机视为一时一地的特殊现象,我却认为,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那场危机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先兆,它警告我们,萧条经济学的种种问题在现代世界里依然存在,并未消失。不幸的是,我当年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这次新版付印时,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美国,正在一场金融与经济危机中拼命挣扎。而且,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困境,当前的危机与“大萧条”更为相似。
亚洲十年前经历的那种经济困境,以及我们所有人时下正在经历的经济困境,恰恰是一种我们自以为已经学会了如何去避免的东西。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发达的、拥有稳定政府的大型经济体(如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也许曾经长久地陷在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但是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间的岁月里,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足以避免上述困境的重现。较小的国家,如1931年的奥地利,也许曾经任凭金融大潮摆布,无力控制本国的经济命运;但现在人们认为,老练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更不用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应该可以在短时间里精心策划出各种救援方案,及早控制危机,以免其蔓延。在过去,当国家银行体系崩溃时,各国政府(例如1930~1931年的美国政府)也许只能站在一旁,束手无策;但在现代世界,人们认为有了存款保险,美联储又随时准备向境况不妙的机构迅速注资,那样的大崩溃应当不会再发生了。虽然任何有头脑的人都明白,万事顺利、高枕无忧的经济时代并没有到来,但我们依然信心十足地认定,不论未来我们会遇到什么经济问题,那些问题都将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问题绝然不同。
但十年前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处在一种经济陷阱之中,假如凯恩斯及其同代人复生,他们会觉得日本的陷阱十分眼熟。亚洲一些较小经济体的遭遇则更加直截了当,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在一夜之间就从繁荣跌入了灾难,而它们所经历的灾难故事,简直就像从一部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史中直接摘录出来的。
当时我对此事的看法是:那就像一种曾经引发致命瘟疫的病菌,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它已被现代医学征服,但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了,而且这一次它对所有常用抗生素都产生了抗体。我在本书初版的导言里是这么写的:“迄今为止,真正被这种刚刚变得无法治疗的病菌感染的人,其实只是少数;但对于我们中间目前为止还算幸运的人而言,聪明的做法应当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新疗法、新预防方案,以免我们最终也沦为它的猎物。”
不过,我们并不聪明。而现在,瘟疫已然降临。
本书新版的许多内容集中于探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现在看来,那场危机是目前正在上演的全球危机的某种预演。但我也增添了许多新内容,用于解释如下问题:美国何以发现自己和十年前的日本颇为相似;冰岛何以发现自己和泰国颇为相似;20世纪90年代经历危机的那些国家何以心惊胆战地发现,它们又一次走到了深渊的边缘。
关于本书
开门见山地说,就本质而言,这部书是一本分析性的简论。本书关注的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事实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应当理解的重要问题是:这场灾难怎么会发生,受灾者怎么能恢复,我们怎么能阻止它再次发生。所以借用商学院的行话来说,本书的最终目标就是揭示“定案理论”,也就是说,要搞清楚我们面前这个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
但我也努力避免把本书写成一本枯燥的理论阐述。本书中没有方程式,没有令人费解的图表,(我希望)也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经济学行话。当然,作为一个声誉良好的经济学家,写那种谁也读不懂的东西本是我的拿手好戏。的确,假如没有我自己以及其他人写的那些晦涩难解的著作的帮助,我很难形成本书所展示的观点。但是,这个世界现在所急需的,是基于充分认识的明智行动,而为了实现这样的行动,我们就必须以平实的方式表达思想,以便使所有相关的大众都能理解,而不是只让那些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读得懂。其实说到底,正规经济学中的方程式和图表,往往不过是用来帮助修建一座知识大厦的脚手架而已。一旦大厦的修建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撤除那些脚手架,只留下通俗易懂的文字。
另外,虽然本书的最终目标是分析,但还是有大量的篇幅进行叙述。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叙述,原因之一在于,“故事情节”,即事件发生的顺序,往往非常有助于我们判断,到底是哪种“定案理论”讲得通(例如,有人对于经济危机持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观点,认为危机只不过是各国经济应得的惩罚而已,但所有这样的观点都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看起来截然不同的经济体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都遭遇危机,如此奇怪的巧合应该如何解释)。另外我也明白,无论要做什么样的阐释,都得有事件的顺序来提供一个必要的背景,毕竟没有多少人花了连续18个月的时间,乐此不疲地关注这场徐徐上演的事件。并不是人人都记得起马哈蒂尔总理1997年8月在吉隆坡说了什么话,并把那些话与曾荫权一年之后在香港最终做的事联系起来;不过,本书将唤醒你的记忆。
我还要对本书的学术风格再说明一点:经济学作家在写作时,尤其是在写作十分严肃的主题时,往往会受惑于一种倾向,就是变得极度冠冕堂皇。我不是说我们考虑的事情不重要,有时这些事是攸关生死的。但太多的情况是,学者们会想,由于一个话题是严肃的,那就一定得庄重地谈论它,也就是说,必须以庄重的言辞来探讨重大问题,随便、轻佻的做法是绝对要不得的。但事实证明,要弄明白那些新奇的现象,你就必须愿意去“把玩”一些想法。我是特意用“玩”这个字的:那些总是正襟危坐、没有一丝怪念头的人,几乎从来不会提出新颖的洞见,经济学上不会,其他方面也都不会。如果我告诉你,“日本正在遭受基础性失调之苦,因为日本国家调节式的增长模式导致了结构性僵化。”那么,你想想看,我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我最多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感觉,就是问题十分严重,没有轻松的解决办法,而这个感觉很可能是大错特错的。但是,如果我来讲一个托儿合作社盛衰交替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确将在本书中多次出现),用这个好玩的故事来说明日本的问题,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可笑,这轻佻的态度也许还会冒犯你敏感的心智,但我这古怪的做法自有目的:它能将你的思路撞到另一条轨道上,比如说,这个例子能让你发觉,至少日本的一部分问题的确是可以用一种简单得令人吃惊的方法来解决的。所以,不要期待一本雍容肃穆的著作:尽管本书的目标绝无半点不严肃之处,但本书的行文将十分轻松随意,这正是本书探讨的主题所要求的。
好了,让我们开始旅程吧,先来看看几年之前我们彷佛身处的那个世界。